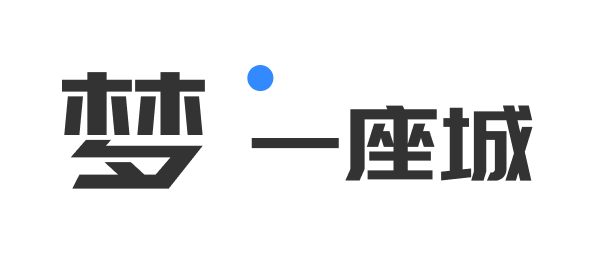「札记」偏见的本质
偏见的本质
我们也许可以将偏见定义为: 对属于某群体的个体持有一种厌恶或敌对的态度,仅仅因为他属于该群体,就被推定具有人们归于该群体的那些令人反感的特性。
过度分类(Overcategorization)也许是人类最常见的思维谬误。我们急于依照极少的事实就进行大规模的归纳。
人类的这个倾向是有其自然基础的。生命是如此短暂,而我们在实践生活中所需要做出的调整又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无法以信息不充分为由停止开展每天的日常交涉。我们必须对面前的新事物定性,判断孰善孰恶。我们无法对世上所有的事物都单独衡量,再做出判断,因而不得不依赖这种粗略而笼统的反应机制。
并不是每种过分的概括都是一种偏见。有些只是误解(misconception),是我们对信息进行了错误的组织。
如果一个人能够根据新的证据修正他自己之前错误的判断,他就是个没有偏见的人。只有在面对新知识时依旧不改变原先的想法的情况下,这种预先判断才算得上偏见。与简单的误解不同的是,偏见会积极抗拒所有可能撼动它的证据。当我们的偏见与现实发生冲突时,我们倾向于意气用事。所以,普通的预先判断和偏见之间的区别是,人们可以不带抵触情绪地去讨论和纠正前者,而非后者。
我们的思维中存在一种奇怪的惰性。我们喜欢轻松地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最轻松的方式,就是将问题迅速归到合适的类别之下,并以此方式预先判断其解决途径。
在两种情况下,一个人不会试图在头脑中启动二次防御机制来维持原有的过度泛化。第一种情况很少见,即习惯性的开放态度(habitual open-mindedness)。有些人在生活中相对较少地应用固定类别框架去评价他人。他们对所有的标签、分类、笼统的说法保持怀疑。他们习惯去了解每种泛化背后的事实依据。在意识到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后,他们对针对族裔的泛化尤其保持警惕。 如果他们坚持某种观念,也是以一种不那么确定的方式,任何与该观念相悖的经验都会修正他们之前的族裔观念。 另一种情况,是出于纯粹的自身利益(self-interest)对概念进行修正。一个人可能从惨痛的失败中明白他的分类是错误的,必须被修正。例如,他可能不知道食用菌的正确分类,并因此中毒。他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而是会纠正他的分类方式。或者可能他开始认为意大利人都是原始愚昧、咋咋呼呼的,直到他爱上了一个出身书香门第的意大利女孩。于是他发现,修正先前的分类方式对自己有好处,之后就建立了更为正确的假设,即世上有各种类型的意大利人。
在特定情境下,从仇恨性的言语表达到诉诸暴力,从谣言到暴动,从流言蜚语到种族清洗,只有一步之遥。 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暴力事件发生之前,人们已经经历了以下的步骤: (1)在经历了长期的明确预判后,受害群体早已被打上烙印。人们开始丧失将外群体成员作为独立个体看待的能力。 (2)针对受害的少数族裔群体长期的言语抱怨、怀疑与批判早已在人们心中扎根。 (3)与日倍增的歧视行为(例如《纽伦堡法案》)。 (4)受害群体成员受到外部的限制。他们可能长期遭受经济匮乏、社会地位感低,易于受到政治格局如战时限制影响,或担心失业。 (5)人们早已受够了压抑,对抗情绪一触即发。他们不再认为自己能够,或者应该去忍受失业、通货膨胀、羞辱和迷茫。反理性主义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人们不再相信科学、民主、自由。他们认可“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he who increaseth knowledge increaseth sorrow)。再见吧知识分子!再见吧少数族裔! (6)有组织的运动吸引了这些心怀愤恨的人。他们加入了纳粹、三K党、党卫军,或者一个不太正式的组织——作为一名暴徒——即使没有正式的组织存在,他们也会设法达成目的。 (7)个体能够从这样的正式或非正式组织获取勇气和支持。他看到他的愤慨是被认可的,他一时冲动诉诸暴力的行为也会能够被他所在的组织合理化——至少他是这样认为的。 (8)一些突发事件发生。零碎的挑衅已经成了过去式,如今风声鹤唳。任何可能是完全虚构的,或者刻意夸大的谣言都可能导致爆炸性的后果。(对于许多参与过底特律种族骚乱的人来说,这场突如其来的暴动源于一个四处疯传的谣言,有黑人劫持了一名白人母亲的婴儿,并将其扔进了底特律河。) (9)当暴力活动发生时,“社会催化”在助长破坏性活动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在看到其他情绪激昂的人群后,个体也会受到交互影响,提高自己的兴奋水平,进一步投身于暴动之中。通常来说,当个体冲动提高时,他的压力会得到释放。 这些都是从言语上的冒犯过渡到公开的暴力之间所要消除的壁垒,也是针对受害者进行身体攻击所需的条件。
人们注意到,参与肉搏、帮派火并、暴乱、私刑、屠杀的主要是年轻人。人们很难想象年轻人在生活中受到的挫折竟然比更年长的人还多,但也许,他们社会化的程度更为薄弱,无法抑制他们亟待释放的冲动。年轻人缺乏长期的社会抑制,对他们来说,重拾婴儿时期的愤怒,通过释放暴力冲动寻求快感更为简单。年轻人的敏捷、精力和冒险精神也使他们倾向于暴力。
有一条颠扑不破的法则,即任何暴乱或私刑的发生都离不开谣言的煽动。谣言参与了暴力模式的某个或全部四个阶段。(1)在暴力事件突发前,关于外群体的误导性言论会不断累积敌意。尤其是当人们听说少数群体有可能参与了阴谋策划、存储武器弹药等活动时。除此之外,种族谣言的爆发式传播往往能反映态势的日趋紧张。评估紧张程度的最佳指标就是收集并调查社区中流传的种族谣言。 (2)当第一批谣言广为流传后,新的谣言会成为暴徒和私刑者的行动指令。他们像是在集结军队一般,高呼 “今晚在河边会有大事发生”,“他们今晚就能抓住那个黑人并杀了他”。如果警方能保持警惕,可能会利用这些谣言来预防暴力事件的发生。 在1943年夏天的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谣言称大量黑人正在谋划在特定的游行节日上发动一场有组织的造反运动。我们几乎能够肯定,这样的谣言会造就一大批心存敌意的白人。 然而警方在事件发生之前,就表达了坚定公开的立场,并为黑人游行者提供了充足的保护,从而消除了一场冲突的威胁。 (3)在较少的情况下,谣言也可能是引燃炸药桶的导火索。流传于大街小巷的流言蜚语,每一次转述后都会变得更为刻薄和扭曲。哈勒姆暴动是通过将一个白人警察从背后向一名黑人射击的故事夸大(事实远没有如此夸张),从而达到谣言的效果。底特律周围流传的大量传闻使整个城市的情绪如箭在弦。在那个有如注定要发生暴动的周日的前几个月中,底特律有关种族冲突的谣言就已经传得沸沸扬扬。广播中甚至还播放了关于一车车武装黑人正在从芝加哥向底特律进发的谣言。(4)在暴乱持续期间,谣言让人们保持兴奋状态。基于幻觉的谣言的传播,尤其令人费解。李(Lee)和汉弗莱(Humphrey)告诉我们在底特律暴力活动到达高峰的时期,警方接到一名女子的电话求助,声称自己亲眼目睹了一群黑人杀死了一个白人。而当警车到达现场时,警方却只发现一群女孩在那里玩跳房子,没有任何暴力活动的痕迹,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该名女子的陈述。然而其他的市民,像这名女子一样,不假思索地相信了这个故事,并开始向外传播。 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个假设,谣言是群体紧张程度的参照指标。对于群体成员来说,谣言只是仇恨言论、敌意的口头表达。所有针对天主教徒、黑人、难民、政府官员、大企业、工会、武装部队、犹太人、激进分子、外国政府等外群体的谣言,都毫无例外地表现出了敌意,并编造出了一些令人反感的特质,以作为产生敌意的缘由。
谣言似乎成为集体性敌意之状态的敏感指标。辟谣作为一种手段——可能并不主流——被用以控制集体中的敌意。在战争期间,报纸上的“谣言诊所”尝试辟谣,并且成功地使人们意识到谣言可能导致的一些危险。然而,谣言的曝光是否能够改变任何根深蒂固的偏见,还有待考证。辟谣所能做到的不过是给予那些温和的,或是仅仅出于疏忽的偏见者一种警告,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谣言的传播对国家利益而言都是百害无益的。
我们所能确定的一点是,排斥某一个外群体的人,也倾向于排斥其他外群体。如果一个人是反犹太主义者,他很可能也是反天主教、反黑人、反所有外群体者。
国家之间的差异是显著的。例如,美国的年轻人比其他国家的年轻人更关注自己的个人生活,对政治和社会发展兴趣较小。(在被研究的国家中)最接近美国年轻人的是新西兰人。然而,与美国人不同的是,新西兰年轻人认为自己的职业前景会和公务员系统联系在一起,他们很可能要为国家效力。美国年轻人则整体上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需要依赖国家的盛衰,也不会想到自己可以为国家贡献些什么。公共和国际事务对他们来说是相对不重要的。 只有采用这种跨国的比较方法,才能够发现美国年轻人是如此“私人主义”(privatism)。该如何解释这一发现?美国的年轻人成长于个人主义传统之中,信奉“人人为己”。幅员辽阔、财力雄厚、实力不容小觑的祖国使年轻人能够理所应当地对未来满怀安全感。对物质财富的重视使他们在制定职业生涯的规划时,更倾向于以最大程度地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为目标。因此,一种对公共生活的淡漠,或者说是“私人主义”,主宰了他们对未来的展望。 然而,我们也不能武断地认为,当国家陷入危机时,美国的年轻人也不会表现出爱国主义精神,或者不愿意牺牲个人物质享受。美国年轻人在报告中反映出的独特的自我中心倾向,在危难时期会让位于更深层的意识形态,这也是美国人“国家性格”的标志。
如果说人类的群体偏见存在任何本能方面的基础,那就是遇见陌生事物时的犹豫。我们注意到婴儿经常对陌生人表现出受惊吓的反应。新生儿出生6到8个月时,如果一个陌生人企图抱起或靠近他们,他们通常会哭泣。即使对方毫无恶意,一个陌生人过于唐突的靠近也会使两三岁的孩子退缩哭泣。面对陌生人时所产生的羞怯经常会持续到青春期。在某种意义上,对陌生人的排斥反应从来不会消失。因为我们保持安全的关键在于对环境中变化的注意,我们对陌生人的出现十分敏感。当我们走进自己的家中,我们甚至可能不会注意到坐在那里的家庭成员,但是一旦有陌生人在场,我们会立刻注意到他,并保持警惕。
如果熟悉的事物是好的,那陌生事物就是坏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所有陌生都会自动变为熟悉。因此,随着逐渐熟识,原本陌生的人往往由“坏”变“好”。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过分依赖“对陌生人的本能恐惧”这个论据,来对偏见做出解释。即使是几分钟的适应都能够减轻幼童对外来者的恐惧反应。
“奸诈”的特质也可能会成为受害者在小处寻求报复的手段。较弱的那一方会倾向于占较强一方的小便宜:黑人厨师可能会从白人女主人家的厨房里“顺走”一些食物,这其中既有实际的物质原因,也有象征性的报复意味。狡猾的形式不仅限于偷窃。它囊括了不同形式的伪装。一个人降低自己的身份,去扮丑角或是讨好,通过谄媚对方获取小恩小惠的行为,既是为了生存,也是一种报复。
针对某些失业男性处境的调查可能有助于解释这样的情况。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研究报告显示,这些失业的男性们感到深深的耻辱。他们把窘迫的境况归咎于自己。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男性并不会因此被责怪。但他们依旧倍感羞耻。西方文化对个体责任的重视可能是主要的原因。我们认为是每一个个体塑造了世界,或者说,我们愿意这样相信。当事情出了差错,个体应该承担责任。所以,移民们会越发为他的口音、扭捏的体态、所缺少的社交礼仪和教育而感到羞耻。 犹太人可能讨厌自己的宗教信仰(因为如果犹太教不存在,他也不会成为偏见的对象)。或者他也可能会鄙夷某一类犹太人(正统保守派、那些个人卫生习惯不好的人或者是商人)。又或者,他也有可能会痛恨意第绪语。因为他无法逃脱自己所属的群体,所以在一种真实的意义上,他也憎恶他自己——至少他会憎恶自己作为犹太人的那一部分。让事情变得更糟的是,他可能同时也恨自己会有这样的感觉。他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由于长久以来的不安全感和紧张,他割裂的自我可能会做出隐秘而自我意识过强的行为。他们将自己作为犹太人被赋予的恼人特质放大,继而自我憎恨,加剧了冲突。这构成了一个永无止境的恶性循环。
群体成员内部的关系经常因群体本身的劣势地位而变得更为紧张。那些采取某种自我防卫方式的人常会对采取另一种自我防卫方式的人表示恼火。万般谄媚的黑人由于“汤姆大叔”般的作风而遭受鄙视。穿长袍、蓄长须的正统犹太人,可能会被现代派的犹太人所排斥,他们的感受有时与反犹太主义的外邦人并无二致。急切想要抹去劣势群体对他们的影响并向往融入主流群体的人,往往会受到群体中其他成员的敌视。他们会认为这样的人是“自命不凡的”“马屁精”,甚至是叛徒。 的确,急迫的、致命的迫害可能驱使所有的团体成员凝聚在一起,让他们暂时放下群体内的矛盾。但是,如果偏见只是处于一个“正常”的水平,内部矛盾就可能被当作一种自我防御模式。
大部分大规模的研究结果都显示,犹太人对少数群体所持有的偏见程度平均而言,实际上比新教徒或天主教徒要低。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其中重要的一点:犹太人,或是其他为偏见所害的群体成员本身的偏见程度不是非常之高(如前几页所述),就是非常之低。他们很少处于一个“平均”的状态。简而言之,作为一名受害者,他可能会发展出对外群体的侵略性,也可能会发展出对他们的同情。这点非常重要。受害者几乎不会处于一个“平均”的偏见水平。普遍而言,他会走向两种极端。他要么以牙还牙,按照弱肉强食的规则对待弱者;要么就是有意识地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他会颇有感悟地说:“这些人是受害者,正如我也是受害者一样。我应该给予他们支持,而不是伤害他们。”
他们往往生活在社会边缘——有时被接纳,有时被排斥。勒温(Lewin)将其比作一种处于青春期般的状态,他们生活在一种未知之中,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主流社会的成年人接纳。动荡与压力所导致的不安和紧张,偶尔会非理性地爆发。而想要变得更为成熟,必须先确认这个世界对自己的态度。许多少数群体成员从未被社会完全接纳,从未对社会充分参与,获得安全感。他们就像青少年一样,没有一个属于他们的容身之处。他们是边缘人。
人们对我们的看法会在一定程度上塑造我们。 如果一个孩子被认为是“天生的小丑”,在众人的称赞和关爱之中,他会不断习得作为一名小丑的技能与诀窍,继而成为一名真正的小丑。如果一个人新进入群体时就认为自己受到了来自他人的恶意,他可能也会发展出带有侵略性与防御性的行为,并引发真正的矛盾。如果我们认为家中新来的女佣手零脚碎,即使事实起初并非如此,女佣最后可能也会出于受到侮辱后的报复心而真的偷窃。 鉴于人们有无数种微妙的方式能够导致某一特定行为的发生,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提出了“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个概念。它引导人们去注意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常会将特定标签赋予外群体,而内群体往往会对这些标签存在一个错误的印象。然而,事实是这两个条件会相互产生影响。我们对他人的感知并不会直接促成他人特质的形成,但却能够对其产生发生影响。我们针对被厌恶群体的印象,会导致这些群体最终展现出这些令人生厌的特质,并坐实了我们对他们最糟糕的期望。这也可能是这些群体针对我们的一些抵触言论所做出的反应。因此,除非双方决意终结这一切,不然这个恶性循环会不断加剧彼此的社会距离,丰实偏见滋生的土壤。
自我实现的预言既可能会促成良性的循环,也可能会导致恶性的循环。容忍、欣赏、赞美将育出善果。受到群体欢迎的外来者可能会对群体做出卓越的贡献,因为他将以诚待人,而不是倍加防备。在所有的人际关系——家庭、种族、国家——中预期效应的力量是巨大的。如果我们预见到了同胞的恶行,我们就倾向于挑起它;如果我们预见到了同胞的善行,我们就倾向于滋养它。
相似的、共同发生或被一并提起的印象,尤其是被贴上相同的标签的印象,很容易被分到相同的类别(泛化、概念)之中。 所有的分类都包含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它们就像森林中的小路,划出了我们的生活空间。 虽然当这一分类方式无法再很好地为我们服务之后,我们会依照经验对其进行修改。但是,根据最少努力原则,只要这些分类已经对我们达成目标起到了正向的作用,我们依旧会倾向于坚持早期的粗略分类。 通常来说,我们会尽可能将所有信息都简化到同一分类之中。 我们排斥变更我们的分类。将与分类不符者称作“例外”这个借口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维持当下的分类(参照)。 类别能够帮助我们识别一个新的对象或个体,并使我们以先入为主的眼光看待它(他)的行为。 由于类别可能囊括了知识(真理)、错误的想法,以及感情色彩,所以类别也可能反映出思维方式是指向性的,还是自闭的。 当事实依据与类别属性冲突时,事实可能会被扭曲(通过选择、强调、解释),以维持我们的分类。
离开了语言,我们几乎无法将对象分类。一只狗能够做出一些最粗浅的泛化,例如“需要避开小男孩”——不过这样的概念只在条件反射的层面上就可以生效,我们不需要对其进行思考。为了在脑海中构建起用以深思、回忆、识别、行动的分类系统,我们需要使用语言将其固定下来。离开了语言,我们的世界就会像威廉·詹姆斯所说的那样,成为一座“经验沙堆”。
一个人带有偏见,首先是因为他在以某种特定方式感知到他对其抱有偏见的对象。然而他的感知方式是由其人格决定的,而人格又被其经历的社会化过程(家庭、学校、社区对其的教养)所塑造。现存的社会结构也是他社会化进程中的因素之一,决定了他的感知。在这些力量之后,还存在着其他同样有效但更遥远的因果影响,这些影响来源于人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结构:个体所生活的国家对其的影响,历史对其的影响,长久以来的经济形势与文化传统。虽然这些因素看起来都很遥远,似乎与偏见行为的即时心理分析是不相干的,但它们仍然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在一个多样性强的文明中,就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分工不同所导致的阶级差异,移民所导致的种族差异,以及许多宗教信仰、哲学观念上的差异所导致的意识形态差异等)。由于没有人能同时代表所有方面的利益,最终人们的见解变得各自不同。人们为了各自的利益或站到一起,或走向对立。
在奴隶制存在的地区,随处可见的偏见行为并不会引人侧目。一旦某种关系被习俗所固化,就很少会发生明显的摩擦。主仆之间、雇主和雇员之间、牧师与其教区居民之间的固定的生活和互动方式都是这样的例子。只有当一个社会中存在社交活动、阶层流动与变化,这个社会才能够创造出“活的”异质性,才会带来偏见。
当每个人都被认为是潜在平等的,并且由国家信条保障了平等的权利和平等的机会时,就会出现一种非常不同的心理状态。即使是最底层的群体成员也被鼓励去努力奋斗,并站出来要求他们的权利。于是就出现了 “精英的流动”。通过努力和好运气,出身较低的人能够不断提升自己的社会阶层,有时甚至能够取代之前的特权阶级。这种垂直流动给社会成员带来了激励与恐慌。
一项实证研究对这一问题给出了相当多的解释。研究人员贝特尔海姆和贾诺维茨发现,一个人当前所处的社会阶层对其所持有的偏见来说并不重要,调节其偏见的更多的是他在社会阶层中的流动方向是向上还是向下。社会的动态流动性被证明比任何静态人口学变量更为重要。这一发现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大多数研究人员都未能发现偏见与人口学变量,诸如年龄、性别、宗教信仰、收入之间存在任何重要的关联。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是否受过高等教育与宽容度之间并无显著相关。流动性似乎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
许多经济、国家间和意识形态的冲突背后都是真实的利益冲突。然而,大多数由此产生的敌对状态产生了额外的负担。偏见模糊了问题,阻碍了核心冲突的现实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被感知的竞争被夸大了。在经济领域,一个种族群体直接威胁另一个种族群体的情况几乎不可能是真的,尽管经常有人试图给出这种解释。在国际领域,由于又增加了不相关的刻板印象,争端进一步被放大了。类似的困惑也笼罩着宗教纠纷。 现实冲突就像管风琴上的音符,它会使所有相关的偏见同时发生共振,而听众几乎无法将纯音和杂音区分开来。
证据的趋势倾向于这样的结论,即了解和认识少数群体成员有助于形成宽容和友好的态度。虽然我们依然无法完美解释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究竟是增进的了解促成了友善关系,还是友善态度促使人们有兴趣了解更多的信息。但是两者间的确存在一些正相关,这是显而易见的。
会引发认同行为的绝不仅限于对父母的爱。即使在由强力而非由爱所主导的家庭中,除了父母,孩子仍然没有其他人可以用作力量和成功的榜样来追随。通过模仿他们的行为和态度,孩子常常能够获得父母的赞扬和奖励。即使没有奖励,他也会模仿父母以获得自信。孩子学他父亲的样子——耸肩、咒骂——这使他感到自己是个大人。 社会价值和态度是认同最易于发生的领域之一。孩子一开始是没有任何“自己的态度”的,因为所有的话题都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他只能去吸收别人的言论。孩子第一次遇到某个社会问题时可能会问他的父母,应该对此持有什么样的态度。他会说:“爸爸,我们是谁?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并且孩子会欣然接受父母给出的答案。从那时起,他就接纳了他的群体身份,以及与这个身份相关联的现成态度。
没有人生来就带有偏见。偏见总是习得的。人们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需求而习得这些偏见。然而,其习得的背景与其人格发展的社会结构是一致的。
偏见程度较高的人可能在任何时候都更容易产生挫败感;甚至可能饱受体质上的困扰。或者,持有高度偏见的人可能对地位有着强烈的需求,并且渴求周围人的认可;当情况不尽人意,无法满足以上需求时,持有高度偏见的人也会经受巨大的痛苦。他们对地位的强烈渴求成为他们目前挫败感和高度偏见的基础。可能是某种内在控制因素导致了偏见态度的差异。持有高度偏见的人缺乏持有宽容态度的人所拥有的一种“哲学”态度。就我们当前而言,我们无须判别哪种解释才是最合理的。我们现有的依据已经足以证明,持有偏见的个体相较于持有宽容态度的个体,更容易感受到挫败感。
有时恐惧的来源不为人知,或者已经被遗忘或压抑。恐惧可能仅仅是在处理外部世界的危险时内心脆弱感的一种不断累加的残余物。受害者可能一次又一次在与生活的交战中失败。因此,他产生了一种普遍的缺失感。他害怕生活本身。他害怕自己的无能,开始怀疑其他人,他认为他人更强的能力是一种威胁。 于是,焦虑成了一种弥散的、非理性的恐惧,而非针对一个适当的目标,它不受自我的控制。就像衣服上的油渍一般,它会污染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并在个体的社会关系之中留下痕迹。因为他无法满足自身的亲和需求,所以他可能对某些人(也许是自己的孩子)变得专制、富有占有欲,同时抗拒其他人。但这些强迫性的社会关系进一步加剧了他的焦虑,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事实很可能证明,煽动者的追随者都是感到自己遭排斥的个体。他们普遍有着不愉快的家庭生活和不满意的婚姻。他们的年龄表明,他们已经活了足够长的时间以对自己的职业和社会关系感到绝望。因为他们在个人或财务资源方面几乎没有积累,他们害怕未来,并乐于将自己的不安全感归因于煽动者挑选出的恶性力量。现实满足感和主观安全感遭到剥夺,使他们对社会持虚无态度,并沉迷于愤怒的幻想。他们需要一个专属的安全岛,满足自身受挫的希冀。所有的自由主义者、知识分子、偏离正轨者和其他可能带来变革的个体都必须被排除在外。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自身也想要某种改变,但是这种改变仅限于能够为其提供个人安全感,并给予其自身弱点以支撑的程度。
煽动言论的吸引力建立在人们先前的态度和与其相一致的态度和信念上;在它的消费者看来,它是权威的;这减轻了他的焦虑。如果煽动信息符合以上所有标准,那就有可能被接受。
煽动者之所以能够得逞,是因为威权型人格的个体需要他们。然而,煽动者这样做并非出于利他的动机,而是为了实现自身的谋划。 在许多情况下,煽动行为是有利可图的。会费、礼物、会员购买的衬衫和徽章都能使党派头目大赚一笔。煽动者能够通过煽动活动赚取财富,而由于管理不善、法律困难或追随者转投其他的新鲜事物而发生的运动失败,也会让一笔可观的财富落入煽动者的口袋中。 煽动者具有政治动机的情况也很普遍。煽动者们通过夸张而含糊的承诺(仇恨言论)而当选参议员、国会议员或进入当地政府部门工作。煽动技巧足以使他们登上报刊头条,或被邀请至电台接受采访,夺人眼球。这些煽动者会因此声名鹊起,在下一次选举中占有优势。煽动者的技巧之一就是唤起希望(例如“分享财富”),或是唤起恐惧,“投票给我,不然共产党人(或黑人、天主教徒)就将控制政府”。正是这两种技巧使希特勒迅速攫取了权力。 但煽动者的动机往往更为复杂。他们也具有受性格制约的偏见。全然冷酷精明、只是在利用反犹太主义攫取利益的政客很少。
克莱佩林(Kraepelin)在对精神疾病进行分类的过程中,将偏执念头(paranoid ideas)定义为“无法被经验纠正的错误判断”。根据这一相当宽泛的定义,包括偏见在内的许多念头都是偏执的。 然而,真正的偏执狂有着难以穿透的坚硬性。他的想法都是妄想,是与现实脱节,并且不受任何因素影响的。
无论这一详尽的理论整体上是否合理,偏执观念的发展史通常包含以下几个步骤:(1)存在剥夺、挫折、某种缺失(如果不是在性方面,那么就是其他高度个人化的方面)。(2)通过压抑和投射机制将缘由完全外化 (偏执狂在其症结所在的领域内完全缺乏洞察力)。(3)由于外部因素被视为一种严重的威胁,这个威胁来源会受到憎恨和攻击。在极端的情况下,偏执狂会对“有罪”者进行攻击或消灭之。一些偏执狂嗜杀成性。 当一个真正的偏执狂成为煽动者,将会导致灾难。如果他在其领导活动中表现得足够正常,行事精明,那么他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妄想体系将会显得貌似合理,他会吸引许多追随者,尤其是那些自身怀有潜在偏执观念的人。一旦有足够多的偏执狂,或是足够多的具有偏执倾向的个体集结在一起,那么就会出现一群危险的暴徒。
偏执倾向解释了为什么反犹太主义者执着于对犹太人和共产党的迫害。偏执狂始终冥顽不化。即使遭到公开的反对、嘲笑、曝光或监禁,他们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偏执观念。也许他们会暂时停止煽动追随者使用暴力,但没有什么能够动摇他的强烈信念,他不苟言笑、咄咄逼人。无论是论证,还是经验都不会改变他的观点。即使有与其观念矛盾的证据浮现出来,他也会扭曲证据以适应自己原来的信念。
宗教的作用是矛盾的。它既会制造偏见,也会消解偏见。虽然各个伟大宗教的信条都是普世的,都会强调兄弟情谊,然而这些信条在实践的过程中往往是充满分裂和残酷的。以崇高的宗教理想之名所进行的可怕迫害,削弱了宗教理想的神圣、高尚。一些人认为解决偏见的唯一途径就是更多的宗教信仰;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解决偏见的唯一途径就是废除宗教信仰。部分有宗教信仰个体的偏见程度比平均水平更高;也有部分有宗教信仰个体的偏见程度比平均水平更低。
法律规范确立了公共良知和预期行为的标准,制止了明显的偏见行为。立法的目的不在于控制偏见态度,而只是限制偏见的公开表达。但是,当表达发生了变化之后,想法也会随之改变,那么长远看也能起到改善偏见态度的效果。
执行得当的法律可能是打击歧视的有效途径。许多法庭的判决也能够取消歧视法条的效力。然而,法律诉讼只能够减轻个人偏见所带来的间接影响。 它无法控制个体的思想,也无法将宽容态度强制灌输给个体。实际上,“你的态度和偏见是你的个人问题,但是你不可以使它威胁到他人的生命、和平、美国公民群体”。法律只能控制狭隘心理所导致的行为。 但是,通过心理学我们能够了解到,外显的行为最终都会对内心的感受与观念产生影响。所以,我们倾向于将立法行动视为减少公共歧视及个人偏见的主要手段之一。
单独的宣泄并非一种治愈,我们只能将其称为一种缓和紧张局势的方式。在说完所要说的话之后,受委屈者能够更好地准备倾听另一种观点。如果他的言论是夸张的、不实的——通常都是这样——那么其所导致的羞愧感能平息他的愤怒,并引导他通过一个更为平衡的视角看待问题。 我们并不建议所有方案都以宣泄的方式开始。这样做会造成负面的气氛。一旦人们需要宣泄时,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而当人们认为自己受到了攻击的时候,则是最为需要宣泄的时候。只有进行了适当的宣泄之后,情况才能够取得进展。领导者的耐心、技巧与运气能够使他们在正确的时刻引导人们以具有建设性的渠道进行宣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