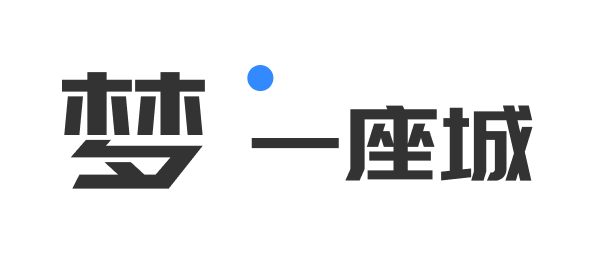「札记」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
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
霍弗认为,投身于群众运动的是一些永久性的畸零人,他们出于某些原因觉得自己的生命已无可救药地失败,因而盲目投身于某种神圣事业,好让个人的责任、恐惧、缺点得到掩埋。至投身的事业是政治也好,是宗教也好,是共产主义也好,是法西斯主义也好,都没有什么关系,只要那是一种有效的运动,可以使他们忘记自己就好。
你无法用理性或道德上的理由去说服一个狂热者抛弃他的大业。他害怕妥协,因此你不可能让他相信他信奉的主义并不可靠。但他却不难突然从一件神圣伟业转投另一件神圣伟业的怀抱。他无法被说服,只能被煽动。对他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他所依附的大业的本质,而是他渴望有所依附的情感需要。
所有群众运动都会激发起其追随者赴死的决心和团结行动的意愿;不管它们宣扬的主张或制定的纲领为何,所有群众运动都会助长狂热、激情、热望、仇恨和不宽容;所有群众运动都能够从生活的某些部门释放出强大的动能;它们全都要求信徒盲从和一心一意效忠。
当我们的生活朝不保夕,完全无力控制我们的生存环境时,就会执着于熟悉的生活方式。我们通过把生活模式固定化去对抗深深的不安全感。借此我们给自己制造了一种幻象:不可预测性已为我们所驯服。
群众运动的吸引力和实务组织(practical organization)的吸引力有一个基本不同处。实务组织可以提供人自我改善的机会,故其吸引力来自它可以满足个人利益。反之,一个群众运动,特别是当它还处于生气勃勃的积极阶段时,吸引到的并不是那些珍爱「自我」、想要把它加强加壮的人,而是那些渴望可以摆脱他们可厌「自我」的人。一个群众运动会吸引到一群追随者,不在于它可以满足人们追求自我改善的渴望,而在于可以满足他们自我否定的热望。
觉得自己人生已败坏到无可救药的人,不会认为自我改善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个人前途的考虑不足以激发他们拼搏,也不足以让他们产生信仰或作出一心一意的献身。他们把自利心理看成是堕落邪恶的,是不洁不祥的。任何出于为己谋的行为在他们看来都是注定失败的。他们最深的渴望是过新生活,是重生,要是无法得到这个,他们就会渴望通过认同于一件神圣事业而获得自豪、信心、希望、目的感和价值感这些他们本来没有的元素。一个积极的群众运动山可以同时提供他们这两样东西。如果他们完全皈依到一个群众运动中去,就会在紧密无间的集体中得到重生,而如果他们只是在旁边敲边鼓,仍然可以得到自豪、信心和目的感这些元素。对失意者来说,群众运动是一种替代品:要不是可以替代他的整个自我,就是可以替代一些能让他的生活可以勉强忍受的元素。
信仰一件神圣事业,相当程度上是替代已经失去了的自信。
一个人愈是没有值得自夸之处,就愈容易夸耀自己的国家、宗教、种族或他所参与的神圣事业。
一个人自己的事要是值得管,他通常都会去管自己的事。如果自己的事不值得管,他就会丢下自己那些没意义的事,转而去管别人家的事。 这神人喜欢搬弄是非、打听试探、越俎代庖,同时对国家和种族事务表现出炽烈兴趣。在逃离「自我」的同时,我们不是会依偎着邻人朋友的肩,就是会掐着他们的咽喉。
热烈相信我们对别人负有神圣义务,往往是我们遇溺的「自我」攀住一艘流经的木筏的方法。我们看似伸手助人一臂之力,实则是在拯救自己。若把神圣义务拿掉,我们的生命即陷于贫乏和无意义。毫无疑问,在把自我中心的生活换成无私的生活以后,我们会得到的自尊是庞大的。无私者的虚荣心是无边无际的。
群众运动最强大的吸引力之一,是它可以成为个人希望的替代品。在一个深受「进步」观念浸染的社会,这种吸引力特别强烈。这是因为进步的观念会把「明天」放大,这样,那些看不见自己前景的人的失意感就会更加深刻。
在现代社会,人们只有在忙得透不过气的时候,才能够不抱希望地活着。失业之所以会带来绝望感,不但是失业者有贫穷之忧,更是由于他们突然发现人生一片虚空。失业者宁愿追随贩卖希望的人,而不愿追随施予救济的人。
当我们个人的利益与前途看来不值得我们为之活下去时,我们就会迫切需要为别的事物而活。所有形式的献身、虔诚、效忠和自我抹杀,本质上都是对一种事物牢牢攀附——攀附着一件可以带给我们渺小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东西。因此,任何对替代品的拥抱,都必然是激烈和极端的。我们对自己只能有有限度的信心,但我们对国家、宗教、种族或神圣事业的信仰,却必定是夸张和不妥协的。一种被温和拥抱的替代品,是不足以取代和抹拭那个我们想要遗忘的自我的。除非准备好为某种东西而死,否则我们不会有把握自己过的是有价值的生活。这种赴死精神可以作为一种证据,向自己和别人显示,我们的选择是最好的。
若是人们接受群众运动的时机已经成熟,那他们参加何种群众运动都有可能,不见得会独钟某种主义或纲领。
社会低等成员之所以能对社会发生重大影响,是因为他们对「现在」全不尊重。他们认为他们的生活和「现在」都已败坏到无可救药,所以随时准备好把这两者加以毁弃。他们也渴望通过某种惊心动魄的集体事业,去掩埋他们已经败坏和了无意义的自我:这是他们倾向于集体行动的原因。因此,他们总是一场革命、集体迁徙、宗教运动或种族主义运动的最早皈依者之一,而他们也会把自己的色彩烙印到运动之中。
这些被遗弃和被排斥的人往往是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的原材料。换言之,本来为建筑师鄙弃的石材会成为一个新世界的奠基石。一个没有废料和不满者的国家,固然会井然有序、高尚、和平而愉快,但它缺少开拓未来的种子。欧洲的弃民竟能远涉重洋来到美洲建立一个新世界,并不是历史开的玩笑——唯独他们能够成就此等事业。
心怀不平者虽然到处都有,但却最常见于下列几类人:(一)穷人,(二)畸零人,(三)被遗弃的人,(四)少数民族,(五)青春期的少年,(六)有野心的人(不管他们面对的是不可跨越的障碍还是无限的机会),(七)被某些恶德或偏执挟制的人,(八)无能者(身或心方面的无能),(九)极度自私的人,(十)对生活厌烦的人,(十一)罪犯。
已经拥有许多而想拥有更多的人,其失意感要大于一无所有而只想拥有一点点的人。另外,只缺一样东西的人也会比缺很多东西的人更不满。
奴隶都是贫穷的,但在奴隶制度普遍存在且行之有年的地方,发生群众运动的机会并不大。奴隶之间的绝对平等,以及奴隶区域之内紧密的团体生活,都让失意感不容易发生。在一个有奴隶制度的社会里,会闹事的不是新遭奴役的人就是刚获解放的奴隶。就后者而言,他们的不满来自自由带给他们的苦恼。
一个群众运动兴起时,其追随者尽管活在一种得严格遵守信条和命令的紧迫气氛中,仍然会有一种强烈的自由感。这种自由感来自他们逃离了他们厌憎、害怕的那个「自我」。这种逃离让他们感觉得到释放与救赎。另外,造就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变迁也带给他们自由之感,尽管这变迁是他们在严格纪律下执行的。
那些觉得自己生命败坏了和荒废掉的人,会渴望平等与博爱多于渴望自由。如果他们为追求自由奔走呼号,他们想要的只是一种建立平等与博爱的自由。对平等的激情是一种对匿名(anonymity)的激情:想要成为构成一件外衣的众多丝线之一,一根无别于其他丝线的丝线。这样、就没有人会把他指出来,与别人比较,让其低劣无所遁形。
在自由实际存在的地方,平等是大众的热望。在平等实际存在的地方,自由是极少数人的热望。有平等而没有自由,会比有自由而没有平等更能创造稳定的社会模式。
极端自私的人特别容易有失意感。一个人愈自私,失望时就愈难熬。因此,极端自私的人往往是无私精神最勇猛的捍卫者。 最凶暴的狂热者,往往是一些本来自私但却出于某些原因(内在缺陷或外在环境)而被迫失去对「自我」的信仰的人。于是,他们不再把高明的利己手段拿来服务其无能的自我,转而用于服务一件神圣事业。但即便他们信奉的是一种鼓吹爱与谦卑的宗教,他们既不会去爱,也不会谦卑。
机会无穷就像机会稀少或缺乏一样,可以是失意感的有力来源。当一个人面对无穷的机会时,无可避免会看不起现在。他会想:「我现在所做或可以做的一切,与我所未做的事相比,就像小钱那样微不足道。」这种失意感特别容易萦绕淘金者和荣景时代的浅狭心灵。正因为这样,一件乍看怪异的事实就产生了:淘金者、掠地者和追求一夕致富者这些明明是最自利的人,往往极乐于表现自我牺牲精神和参与群体行动。基于这个缘故,面对无穷机会的人要比那些选择有限、只能过按部就班生活的人更能接受爱国主义、民族团结甚至革命的宣传。
在一个行将被同化的少数民族中间,最有成就和最没成就的两类人又会比成就中庸的人感到更大的失意感。失败者本来就易于自视为边缘人,而如果他又是少数民族身份,他的失败会让他的无归属感更加浓烈。同样感受也会出现在少数民族的成功者身上。他们尽管有名有利,却往往难以打入多数民族的圈子,这使得他们格外意识到自己是个外人。另外,他们因为成功而自感优越,所以痛恨暗示他们低人一等的同化过程。由是可以推论,在一个行将被同化的少数民族里,最容易被群众运动吸引的,是最有成就和最没成就的这两类人。在意大利裔的美国人之中,最仰慕墨索里尼的是这两类人;在爱尔兰裔美国人中间,对德瓦莱拉(De Valera)的呼吁反应最踊跃的也是这两类人。对犹太复国运动支持最力的是最有成就和最没成就的犹太人。最有种族意识的美国黑人是成就最高和成就最低的黑人。
「爱国主义是歹徒的最后归宿。」——这句挖苦话并非全无道理。狂热的爱国主义和宗教或革命的激情一样,常常可以作为罪恶感的抚慰之所。说来奇怪,不管是伤害者或被伤害者、犯罪的人或被侵犯的人,同样可以在群众运动中找到一个逃避他们污染了的人生的出口。看来,悔恨与悲愤都可以驱使人走向同一个方向。 群众运动有时看起来简直是为罪犯的需要量身订造:它们不只可以「净化」罪犯的灵魂,还可以让他发挥性向与能力。群众运动的宣传手法是唤起信徒一种悔罪罪犯般的情绪与心灵状态。
群众运动的策略,是要把一种病传染给人,然后又把自己说成治病的药方。一位美国牧师就感叹说:「我们美国神职人员的工作有够难:向一群大都没有真正罪恶感的人传扬救世主的福音。」一个有力的群众运动会培养其追随者的罪恶感。它不但会把人的自主「自我」形容为贫乏和无助的,还会把它说成是罪孽深重。悔罪的方法是抛弃个人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得救的方法是把自我掩埋在团体的神圣一体性中。
在把时代的一切痛骂得一文不值以后,失意者的失败感和孤立感会获得缓和。你仿佛听到他们在说:「不只我们是没有价值的人,就连社会中最快乐最成功的那些,也是不值一哂,虚空度日。」换言之,通过贬抑现在,他们获得了一种隐约的平等感。
失意者会在大混乱和有钱人的没落中得到快乐,不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已经为兴建一个新世界铲除了一切障碍。他们固然狂热地呼号「要么一切都变得美好,要么一物不留」,但他们心里真正热望的,大概是「一物不留」。
而「忠实信徒」之所以能够在面对周遭世界不确定和不怡人的真实时屹立不动,正是因为他们自信奉行的是绝对正确的教义。
一种能理解的教义会缺少力量。一旦我们理解一样东西,它就会像是发源于我们自身。显然,那些被要求抛弃自我的人不会从发源于自我的东西上看到永恒确定性。凡是他们能完全理解的东西,其有效性与确定性在他们眼中都会失色。
如果一种教义不是复杂晦涩的话,就必须是含糊不清的;而如果它既不是复杂晦涩也不是含糊不清的话,就必须是不可验证的;也就是说,要把它弄得让人必须到天堂或遥远的未来才能断定其真伪。哪怕一套教义有某个相对简单的部分,信众还是会把这个部分加以复杂化和晦涩化。简单的字句会被解释得无比复杂,使之看起来就像蕴含着什么秘密信息。因此,即使最有学问的「忠实信徒」也会有点文盲的味道。他喜欢罔顾一些字的真义使用这些字,并养成诡辩强扯、吹毛求疵、钻牛角尖的爱好。
一个积极的群众运动会否定现在,把目光集中在未来。它的力量正是衍生自这种态度,因为否定现在让它可以对现在的一切——其信徒的健康、财富和生命——无所顾惜。它必须装作已经把未来之书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它的教义被宣称是打开这本书的钥匙。
狂热者永远会觉得自己不完整和不安全。他无法从自身——也就是他排斥的「自我」那里获得自信,而只能从他凑巧碰上和热情依附的神圣组织得到。热情依附是他盲目献身与笃信的根本,被他视为一切德性与力量的源泉。虽然他这种一心一意的奉献究其实是为了给自己的生命寻找支撑,但他往往会把自己视为他所依附的神圣伟业的捍卫者。他也准备好随时牺牲性命,以向自己和别人显示,他扮演的真的是捍卫者的角色。换言之,他牺牲性命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
你无法用理性或道德上的理由去说服一个狂热者抛弃他的大业。他害怕妥协,因此你不可能让他相信他信奉的主义并不可靠。但他却不难突然从一件神圣伟业转投另一件神圣伟业的怀抱。他无法被说服,只能被煽动。对他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他所依附的大业的本质,而是他渴望有所依附的情感需要。
以下的道理不难理解:当我们受到伤害、渴望报复时,总会希望有别人站在我们同一边。但让人费解的是,当我们的恨不是出于明显的理由,而且看来是站不住脚的时候,渴望盟友的心理会更形迫切。而这种恨,也是最有力的凝聚剂之一。 这一类不可理喻的仇恨是从何而来,它们又为什么能发挥凝聚的作用?它们是我们拼命要掩盖自己的贫乏、无价值、罪恶感和其他缺点的一种表现。自卑就此被转化为对他人的怨恨。而为了掩饰这种转化,我们会作出最坚决和最持久的努力。显然,最有效的掩饰方式就是找一些人——愈多愈好——来恨我们所恨的同一对象。看来,我们要宣扬什么主义信条时,真正要别人接受的不是我们的特定信仰,而是我们那种不可理喻的恨。
去伤害我们恨的人,会让我们的恨火上加油;反之,宽大为怀地对待一个敌人,会削弱我们对他的恨意。
任何崇高(sublime)的宗教必然会让信徒产生强烈的罪疚感。这是因为高不可攀的理想必然会带来实践上的落差。由此看来,一种宗教愈崇高,它孕育出的恨意就愈凶猛。
恨一个有不少优点的敌人要比恨一个一无是处的敌人容易。我们无法恨那些我们鄙夷的人。
团结性和自我牺牲精神这回事本身就足以诱发仇恨——哪怕当初它们是以最高尚的手段培养出来的。即使一群人的结合是为了鼓吹宗教宽容与世界和平之类的崇高目标,一样会对意见相左的人极不宽容。 这是因为,如前所述,个人舍弃自我乃是他产生无私心理和完全融入一个集体的先决条件,但舍弃自我的人极容易产生各种激情,其中包括仇恨的激情。在团结和无私的环境中,还有别的因素可以促使恨意的滋长。那就是,自我否定的人很容易会觉得他们有权利对别人冷酷无情。我们一般会觉得「忠实信徒」——特别是宗教上的忠实信徒——都是谦卑的人。但事实上,顺服和谦卑会孕育出骄傲与自大。「忠实信徒」很容易会自视为被上帝拣选的人,是地上的盐,是世界的光,是伪装柔弱的王子,注定要继承地上和天上的王国。与他信仰不同的人是罪人,不肯听从他的人将会灭亡。
最容易单凭宣传打动的一种人是失意者。他们的恐惧、希望和激情把五官给闭塞住,把他们与现实世界隔离开来。他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他们想象出来的事情,而在宣传家鼓动的言辞中,他们听到的是自己灵魂发出的音乐。事实上,感情奔放的胡言乱语和响亮的口号,要比逻辑无懈可击的精确言辞更能引起失意者的共鸣。
传道或传扬一种主义,乃是寻找一种尚未找到之物的激情,而不是把已有之物带给世界的渴望。它是为了寻找一个终极和不容反驳的证明,以证明我们拥有的真理是唯一和独一的真理。狂热的传道者是要通过转化别人强化自己的信心。
一旦舞台布置就绪,一个卓越领袖就是不可少的。没有他,就不会有群众运动可言。环境的成熟并不会自动产生一个群众运动,选举、法律和政府组织亦无此能力。
所有群众运动都会利用行动作为促成团结的一种手段。一个群众运动之所以要散播和鼓励斗争,除了是为了整垮敌人,也是为了撕下追随者身上的个体特殊性,让他们更完全地融于集体中。
一个鼓励行动的群众运动可以唤起失意者的热烈反应。因为失意者把行动视为医治他们烦恼痛苦的良方。行动可以让他们遗忘自我,让他们有一种目的感和价值感。
因为深谙自己的瑕疵与缺点,失意者对别人的歹意与恶念总是特别眼尖。一个有自卑感的人特别容易看出别人的短处。如果别人身上有我们自己竭力隐藏的那种瑕疵,我们总是不遗余力去加以揭发。所以,当一群失意者因一个群众运动结合在一起时,总是会弥漫出强烈的猜疑气氛。值得惊异的是这种同侪间病态的互不信任不但不会带来分裂,反而会带来强固性。这是因为知道自己被持续监视,群体中每一个成员会热烈遵守行为与思想守则,以避免受到猜疑。因之,互相猜疑对维持严格正统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热烈的信仰。
能为一个群众运动做好铺路工作的,是那些善于使用语言和文字的人;但一个群众运动要能实际诞生出来和茁壮成长,却必须借助狂热者的气质与才干;而最后可以让一个群众运动获得巩固的,大半是靠务实的行动人。